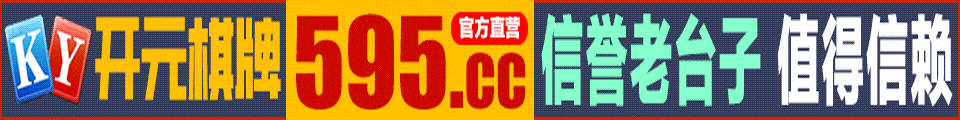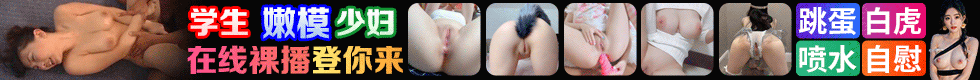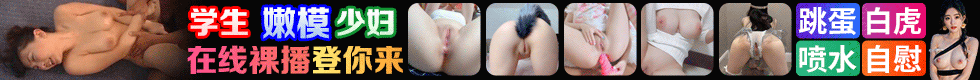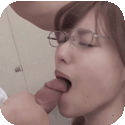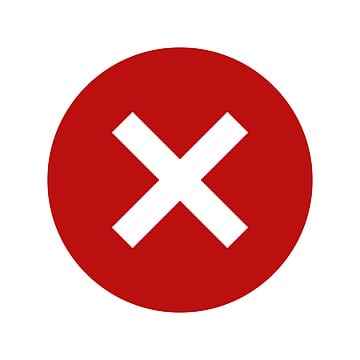这一切完全是偶然发生的,那是一个星期五晚上,在市区里的皮革俱乐部里, 我看见了两个不是很熟悉的家伙,两个非常性感的家伙。我大约25岁,刚刚来 到这个城市不久,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社交活动也很少,那天晚上我穿著便 服,紧身型的牛仔裤,扣子型的泰勒牌皮带,白色的圆领体恤衫,白色的棉 袜,合身的皮夹克。我们的眼光接触到了一块,互相交换了几个眼色然後便走 到一起了,我们安静的交谈了一段时间,他们暗示我靠近他们,我毫不犹豫的 照办了。他们都比我要略大一些,都是高个子,黑头发,使人难忘的极具吸引 力的外表,穿著黑色的皮衣和粗布斜纹布料的衣物。他们自我介绍,一个是 博,一个是金。博是律师,金是自由程式师,专门设计和制作网页。 博的发型是那种大兵式的短发。我很喜欢,我的那个很有魅力的老板也是这种 发型,博让我用手去摸他的头,我略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还是照作了。金说我 如果也是理博的那种发型,看上去也会很不错。我从没想过要理这种发型,不 过金的这个提议我瞬间就接受了,我告诉他我下个星期只要有空就会去理。 站在他们两个中间,感受著博的发茬,我感到了一点点的胁迫感,不过马上就 被更加强烈的性的冲动征服了,他们也明显的感到了这一点裤。随著我们之间 的熟悉感的增强,我们开始由口头的交谈更进一步为身体的接触,他们用手来 感触我的身体,命令我采用立正的姿势。我们之间的闲聊变成了一次正式的会 面,他们问了我所有他们想问的问题。他们问我是否曾经被捆绑过。单单只是 这个问题就让我的阴茎的硬度有所增加,我回答说是,而且不止一次,并且我 很喜欢捆绑。他们告诉我,他们两个都是“主人”的角色,而且在捆绑和调解 上的口味都比较重,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奴隶男孩”。我不知道我应该对 他们的话有什么反应。“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 念。他们继续告诉我他们曾经有过很多个长期的“奴隶”,他们觉得我很有潜 质,很符合他们的要求:可爱,小个子,身体的比例协调,是一个可以在身体 上很容易支配的“男孩”,并且很有可能在心理上也具有奴隶的性质,能够在 调教的游戏中得到满足和快乐。他们很高兴我曾经有过关於捆绑的经验。在这 个会面的过程中,我详细的向他们描述了我以前的被捆绑的经历和我关於捆绑 的幻想,然後我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那些迷人的刺激的问题:是否被独自的留在 家里,整夜的处於不可逃避的束缚之中?我所接受的最长时间的捆绑有多久? 我是否被堵住嘴?有没有被捆绑起来关在笼子里睡觉?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关於捆绑和“奴隶男孩”的内容超越了一切。我有些怀 疑那种做法的现实性,我有些害怕将我自己置身於其中,但是同时我的内心越 来越兴奋,我的心砰砰的跳著,非常想玩弄我自己的阴茎,最终我使他们相信 我能够承受他们所想要做的一切,甚至没有认真的考虑这一切的实际的含义。 我听见我自己告诉他们我这个周末没有安排,而且在星期一上班之前不需要回 到城里,我十分渴望同他们一起在他们郊外的住所度过周末。他们向我提出了 一些基础的要求并向我一再的声明服从他们的重要性:捆绑,通常是很严厉的 捆绑,由他们选择;他们认为不存在任何的限制,他们将会根据我身体的反应 来决定对我的调教程度;完全的毫无疑问的服从;除了他们的要求之外,说话 和交谈是禁止的。如果这个周末我觉得不能承受,我将会有机会选择离开。我 将不能再教他们的名字,取而代之的称呼是“主人”。 离开了俱乐部,我安静的跟随他们走进了他们的大篷车。他们的身体好像可以 对我起到催眠的作用,同时他们的严肃的态度,他们对游戏规则的描述同样使 我迷失。同他们交谈的欲望被想要遵守规则保持安静的欲望征服了。我的阴茎 在内裤里僵硬的象一根铁柱。当我们全部走进他们的昏暗的大篷车里之後,他 们让我脱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後跪在看上去象一块厚厚的毯子上,那是一个 睡袋。它的外表感觉上很粗糙好像是简单加工的那种,他们将我的双手铐在背 後,将我的脚踝用绳子绑紧,在这个过程中,我努力的保持身体的顺从和挺 直,博用力的压住我的头然後固定上了一个内置有一个橡胶球形口塞的头具。 我永远都记著这些兴奋的镜头:裸体,无助的捆绑,被强迫张大嘴巴,带上橡 胶的口塞,两个有权威的迷人的家伙,我甚至和他们不是很熟悉,控制著我的 身体。我的阴茎已经坚硬到了它的极端,甚至有些疼痛了。它在我的内裤里膨 胀到了它的极限,顶住了我的腹部。 两个主人(2) 依然保持著跪姿,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後,双脚被并拢绑紧,我将屁股放在双腿 上休息,直到博要求我跪直(“跪式立正”)。然後他用力将我的阴茎下压, 几乎压倒了我的两腿之间,然後他突然松手,看著它迅速的弹回到我的腹部。 金则用中指轻轻的探击我的阴茎,看著它左右的摇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得 意的笑著,然後轮流用这种方法玩弄我的私处,知道我被堵住的嘴里发出咕噜 声,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向他们发出我即将射精的警告。於是博走到我的身 後,去了车尾,金向我解释到在没有得到他们确切的允许之前,我是不能射精 的。博走回到我的面前,带著一个皮质的护身样的东西,并且上面还有一些金 属的连接物用於加固。金将我的阴茎向下压到了一个特定的位置,博则将这个 皮具扣在我的腰间和两腿之间。皮具的内部有一排金属环,套在了我的阴茎 上,使它保持著一个向下的位置,博则将皮具上所有的皮带全都收紧。金同时 给我带上一个皮质的头套,压在已经戴著的面具上,只有在鼻子的位置有一个 供我呼吸的小孔。我再也看不到了,他们帮我俯卧著,全身伸展开来,睡在睡 袋里。当他们中间的一个开车的时候,另外一个将我从脖子以下的部位包裹在 睡袋中,我能感觉到绳子从睡袋外绑住了我的双脚,膝盖,腰和胸部。然後我 觉得睡袋的顶端包在了我的头上,我被翻了个身,睡袋完全的将我密封在里面 了。想到我头部的球形口塞,皮革头套,和睡袋,我瞬间觉得有些窒息了,不 由自主的开始蠕动,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让我安 静下来,减少活动,并告诉我我有足够的空气可以呼吸。慢慢的我开始平静下 来,他是对的,只要我放慢呼吸的节奏,窒息感就消失了。一会儿,我又被翻 了过去,更多的绳子将我完全的固定在车厢的地板上。 我可以估计到车的行程大概花了一个钟头。这一个小时里,大部分的时间我感 到有些迷茫,但是那种强烈的由於捆绑而带来的性欲是真实的。事实上我完全 的深陷在严密的捆绑之中。我的印象里我多么的希望我的阴茎可以不再坚硬, 以解除在皮革的囚禁下的勃起所带来的痛苦。车停了,我感到博和金将我从地 板上解开,连著睡袋一起将我抬进了屋子,经过了一段楼梯,把我放在了什么 东西上面,然後将我脸朝下在那个东西上扣牢。现在回顾起来,他们是用了一 条皮带将我固定在军用的帆布床上。他们将我留在床上(很有可能是独自一 人),过了一会儿,我想看看到底我能有多少的活动空间,我开始收缩蠕动, 显然想从这种束缚里逃脱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并不是我原来计画中的一部分。 我的肩膀开始疼痛,并且由於我的挣扎,使我在睡袋了觉得很热。我到现在还 能够记得我的阴茎上的痛苦(它一直在皮质护身里保持勃起的状态);我开始 有些担心我是不是将我自己置入了一个比我能够承受的要严重的多的环境,并 且担心我到底还要在这个睡袋里待上多久,感受著几乎?薹ㄈ淌艿奶弁春椭? 息。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我的双脚被松开了,然後是其他的部分。当他们彻 底的将我从睡袋里解放并摘掉了头套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动作和配合是非常 熟练的。我身处在一个地窖里,琳琅满目皆是捆绑和束缚用具。我记得我顿时 打了一个寒战,那是一种兴奋於忧虑的混合。 他们一起松开在运输途中所使用的束缚物,换上了另外的一套捆绑用具,一个 皮项圈,一个皮面具,上面有一个宽大的口罩,口罩的中央有一个卵形的牙 托,使我的嘴张开;小皮拳套,一套皮带将我的双手固定在背後并向上高高的 吊起和项圈上的D形环连在一起,固体连接的脚镣,使我的双脚保持著18寸的距 离。尽管皮面具部分的阻挡了我的视线,在我的努力下我还是可以看清我的身 体。从皮质护身中得到了解放,我的红色的粗大的阴茎再次跳入了我的视线, 那些金属环所造成的印痕依然历历在目。我的嘴没有被堵住,不过我保持著沉 默,那是他们先前就向我声明过的。在他们的指令下,我蹒跚的移动到了两条 长凳之间,跪下。在我被帮在行军床上的时候,他们已经脱掉了衣服。他们两 个都只穿著黑色的长筒皮靴和皮套裤,他们的胸部和生殖器暴露在外面。在我 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全新的捆绑和仔细欣赏他们火热的身体时,他们开始下命 令了,首先是跪式立正,然後是弯腰向前倾斜。金坐在我的前面,他通过项圈 上的D形环控制我的头部,他让我开始为他口交。他批评我的技术,於是坐在我 身後的博命令我翘高皮股,用一个皮浆击打。他们交换了几次位置。我用力将 舌头伸出口罩的开口部分,不过那个牙托却限制我嘴部的活动,使我很难很好 的完成我的任务,尤其是博的阴茎,特别的粗壮,金调整了面具的松紧程度, 以便我的嘴张的开一些。最终,他们都得到了满足,不过他们警告我必须提高 我的技巧。 依然保持跪姿,我被命令跪式立正,金帮我转了一个方向,使我对著一面墙上 的大镜子,博来到了我的眼前,拿著一个看上去象一个肛门塞的黑色橡胶口 塞,锥形的,底部很宽,连接著皮带。在他的指示下,我将嘴尽可能的张大, 他将口塞的顶端慢慢的插入口罩,当口塞完全插入後他将口塞上的皮带和面具 绑在一起,在脑後将皮带收紧。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有效的堵嘴方式,我的 嘴被完全的充满了,口塞中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使我可以用嘴得以正常的呼 吸。他们给我带上乳头夹,然後使用了一条皮带将我的阴茎根部扎紧并将我的 两个睾丸分开,然後在上面挂上了一个重物,使我的阴茎笔直向前,而不是紧 紧的贴著我的腹部。金在我的阴茎上夹上一些夹子,然後博蹲在我的侧前方用 一条小皮鞭鞭打我的大腿内侧。金蹲在另外一侧对我说我可以在博刺激我的阴 茎的时候射精,并且我比自己想像中还要性感,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奴 隶”,成为我的生殖器的奴隶。博加入了谈话。他们告诉我我可以从镜子里面 看到一个真实的自我,一个天生的奴隶,需要他们的捆绑,堵嘴,羞辱和囚 禁。他们告诉我,我的阳具是一个“奴隶的阳具”,它的存在就是为了他们的 使用,它将被训练,只在他们的命令下才会射精。过了一会儿,一些夹子开始 松动,提高了我的敏感度,我开始蠕动,呻吟,双手在背後扭动,这也增加了 项圈给脖子带来的压力。金抓住我使我不会摔倒,然後我体验到了最为痛苦同 时我最为兴奋的高潮。无法控制的,抽搐著,我射的遍地都是。 高潮过後的几分钟里我简直就是昏迷的。当我的知觉恢复的时候,他们将我拖 到的浴室。他们拿掉了乳头夹和我阴茎上的束缚,不过其他的捆绑依然如旧, 他们让我站在便池旁,让我排尿,在经过了好几次的努力後我才成功。博想将 我半硬的阴茎装入一个鸟笼中,我认得那是一个贞操装置,不过我的阴茎再次 膨胀的太大了,於是他停了下来,换了另外一种贞操带,像是一个手铐上连著 一个金属管。我的阴茎开始变硬了不过还没有完全的不听指挥,於是他可以把 它通过润滑後塞到金属管里。当金取出一个中号的肛门塞放在我的眼前并问我 想不想先清洁一下时,我有些害羞的点了点头。他们使用了速效的灌肠剂,然 後饶有兴致的看著我排除体内的污秽,接著用肥皂和清水将我洗的乾乾净净, 他们的服务让我觉得更加的害羞。他们让我跪低,让我翘起臀部。由於是刚刚 射完精,我很难适应那个肛门塞的入侵,他们很有耐心,慢慢的将肛门塞完全 的插了进去,只剩下底部露在外面。他们帮我站直,将贞操带完全的锁上,并 提到这种装置叫做“阴茎铐”,阴茎铐底部的皮带正好压在肛门塞上,防止肛 门塞的滑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蹒跚的走出了浴室,来到一个钢制的笼子 前,他们一起使我开始了“睡眠时间”。头具和口塞还是保持原位,不过拳套 和手臂的束缚解除了,他们给我穿上了皮革的束缚衣,我的双手在身前交叉, 前臂被绑在一起。束缚衣感觉比较舒服,暖和但不是太热。博熟练的使用著束 缚衣上的皮带,把它们到处固定扣牢,特别是我的腹股沟。金打开了固体连接 的脚镣,换上了皮质的连体脚镣。当他们帮我左右挪动著钻进笼子後,他们特 别摆了一个姿势,然後关上并缩住了笼子的们,告诉我要睡觉了。我看著他们 离开,听到他们上楼,然後所有的灯都关掉了。(未完待续 笼子里的地板上铺著海绵垫,有一个小小的枕头。我精疲力竭,无法考虑我目 前的一切,很快就睡著了。我梦到我被束缚著无法移动双手,突然我惊醒了, 全身都是冷汗,而且我发现梦里的一切全部是真实的。我开始思考,开始质疑 我的判断。金和博说得对吗?我是一个天生的奴隶吗?我到底内心里想要什 么,被单独的遗弃,带著面具,口塞,穿著束缚衣,被陌生人锁在地窖里的笼 子里?我的阴茎还是那么坚挺,一点都没有软下来的迹象,紧紧的贴著贞操带 上的金属管,在它允许的范围内勃起著。努力的集中著我的注意力,我艰难的 吞咽著口水;紧紧的面具和粗大的口塞使我的牙齿和嘴隐隐作痛;我的括约肌 不受控制的有节奏的夹紧肛门塞;双手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满身的汗水, 我觉得很热,很不舒服,束缚衣里面的我已经全身湿透了;然而我的阴茎在这 种很难受的状态下还是努力的在变大,这使我觉得我的龟头已经伸出了那根金 属管,不过太黑了,我无法看到。 天花上的灯突然亮了,我再一次的醒了过来,今站在笼子的前面。我觉得天边 已经有了一丝曙光,从地窖里的小窗子里隐隐的透了进来。我的感觉告诉我这 时还是晨。金打开笼子,命令我并帮助我站了起来,当然,由於全身的不自 由,这是很困难的。他拿著一个空的塑胶袋;他把它放在了阴茎铐的金属管下 面。几分钟之後,在他的努力下并且在他的惩罚的威胁下,我排泄了出来,他 把塑胶袋移到我的鼻子下让我闻了一会儿,然後丢到了一边,他抓住了我一只 胳膊,让我跟著他走。我几乎是在一跳一跳的走,脚踝上的皮铐之间的连接太 短了,限制了除此以外的任何活动方式。我在墙上的一面大镜子里完全的看到 了我自己的模样,束缚衣,头具,跳著脚。我的心里混合著羞辱和兴奋的感 觉,这是我?崭张磐昴虻纳称饔挚荚谒念碜永锊稹=鸾掖降亟牙? 的一个壁橱前。我的全身打了一个冷战,心怦怦地跳,因为我看到了壁橱里的 全套的装备,并且可以想像它们在等著我去受用。金把我放倒在壁橱的下面一 块厚厚的帆布中央。他让我坐好,膝部弯曲,紧贴在胸前,压著我的双手(束 缚衣使我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拉扯著帆布,开始象邮局里包裹东西一样 将我包了起来。眼前突然的一片黑暗,?冶宦木倭似鹄础5蔽冶坏醯娇罩? 後,帆布袋紧紧的贴著我的身体。我感到金的手抚摸著我的背,肩膀,和大 腿,他转了转袋子,检查了一下我在里面的位置,然後用浓厚的低音告诉我一 个真正的奴隶(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个词)会很喜欢被独自一人吊在袋子里。他 说他和博在早餐前要出去办点事,他们相信我一定能从吊著的过程中得到快 乐。然後门关上了。 回想起来,我还是不能确定他们两个真的把我一个人吊起来後独自留在家中。 不过当时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让我一度十分的忧虑。我想,在前一天晚 上我对他们表了态之後,他们一定认为我可以承受这一切。我的心里感到被遗 弃,我的身体就像是一件没有生命的货物体验著这一晚各种各样的捆绑和束 缚。金离开时的言语暗示我应该对这一切表示感激。以前也曾经有一个朋友把 我装在邮包里吊起来,不过时间很短,而且那时我的身上并没有其他的束缚, 我的朋友也没有走开,而是一直在我的身边。这一次,束缚衣和其他的刑具加 强了邮包所带来的紧迫感,让我体验到了狭小的,火热的空间和稀薄的空气。 当我想伸伸腿或是伸展一下时,我的重量会使我在空中摇摆,并且邮包的内里 更紧的贴著我的身体。帆布上有著皮革的加固,当然也有通气孔。在黑暗中, 在难熬的热力中。我期待著他们回来。我的手痛苦不堪,汉像是小溪一样在我 的束缚衣里不停的向下流淌,我的下巴好像脱臼了一样,我的整个阴部紧张的 压著那个铐子。更糟糕的是,我的体重将那个肛门塞一点点的更加深入到我的 体内。我尝试著从严密的头具和口塞中发出含糊的呻吟“请饶了我吧,主 人”,不过没有任何回应。 对於当时的我来说,那是永远的,不过最终门开了,传来了声音。我无法区别 他们,不过当其中的一个向我说道如果我觉得还没呆够的话,他们可以让我再 享受几个小时的时候,我迫不及待的发出呻吟声,并开始不停的扭动。他们互 相交谈了一会儿,然後威胁到如果我还该制造杂讯的话,他们就会让我在这里 吊上一整天。於是我停止了蠕动作为我对他们的反应,他们把我放到了地板 上,并将我放了出来,我完全的屈服了,我伏在地上,伏在壁橱里,挨著他们 的脚旁。金弯下腰,解开了头具拿出了口塞,命令我舔博的靴子。我的嘴被堵 住了一整夜,完全是乾燥的,所以我很难舔,不过我想都没想就照作了,看来 羞辱已经习以为常了。 博和金把我架了起来,离开了壁橱让我坐在一个海绵垫上。他们松开了所有的 束缚,除了肛门塞。博用他的脚趾捅著我的生殖器,它早就不听使唤了,当阴 茎铐移开的一霎那,它就自做主张的挺了起来。他们给了我一大杯水,让我用 一根吸管慢慢的吸吮。他们得意的告诉我,我的“奴性的阴茎”显示出我事实 上是一个很好的捆绑奴隶,他们发誓今後还会将我吊起来。 他们让我穿上了鞋袜,博在我的脖子上带上了一条宽皮项圈。警告我一定要让 肛门塞保持原状,地窖里有一些健身设备,他们让我在一个跑步机上锻炼一下 并用吸管喝水,同时他们做著一些力量练习。 我的半硬的阴茎在身前摇摆,我非常愉快的在跑步机上行走,感受著身体的自 由,尤其是双手的自由。这种愉快的活动大约持续了30分钟左右,由於被堵了 一整晚,我想轻轻的通过肛门塞排除体内的气体,不过它开始向外滑落。我慌 忙的将手放到背後,想抓住它,将它再插回去,同时还不能让跑步机停下来, 但是肛门塞无情的滑过了我的手指,掉到了跑步机上,然後弹到了地上。金向 我宣布我将受到惩罚。博消失了一会儿然後带著一大堆东西回来了。金坐在练 习凳上,我伏在他的大腿上,他们将我的双手迅速的用绳子紧紧的绑住,绑的 都感到了疼痛,然後拉向上到我可以承受的极限,在?钊?系型环里扣牢。然 後他们再次使用了那个组合型的头具和口塞(昨晚在车上用的那个)他们润滑 了我的肛门,慢慢的插入一个大号的肛门塞。那不是很容易就插的进的。金用 力打我的屁股并要求我放松。终於在一下撕裂的疼痛中,肛门塞的最突起的部 分通过了我的括约肌,进入了我的後门。他们帮我站好,又用了一条对折的绳 子捆在我的手腕上,将末端沿著背部向下然後穿过我的胯下,沿著屁股缝紧紧 的压著肛门塞,用剩余的部分捆扎我的阴茎和睾丸,然後在那条绳子上用力拉 了拉,试了试它的松紧度,让我回到跑步机上继续锻炼。这一次可就没那么舒 服了,我的胳膊被高高的吊绑在背後,很难控制身体的平衡。只要我一不小心 将我的手稍稍的移动,我就觉得我被人卡住了脖子,而且我的生殖器被什么东 西碾碎了一样。我只能略微的弯著腿来减轻阴茎和睾丸上的痛苦。偶尔的,金 和博还会将跑步机的速度加快,然後在一旁悠然自得的观察我的出汗,观察我 通过头具和球形口塞艰难的喘气。(未完待续) 锻炼完了後,他们松开了绑绳,将我的手铐在前面,然後把我放到笼子里,观 察我进食。他们给我做了一些煎蛋,一些水果玉米沙拉,一杯橙汁,我把这些 东西溅的到处都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试过被铐著双手吃东西。当我盘腿坐著 的时候,肛门塞的压力让我更清楚的感受到它的存在,我的阳具直挺挺的向上 翘著。吃完後,他们命令我走出笼子,把我的手重新反铐在背後,带著我到了 浴室。他们帮我脱掉了鞋袜,让我戴著手铐淋浴。他们抚摸著我身上所有的器 官,这让我觉得十分的怪异和窘迫(金甚至给我刷牙)。他们看来对这种角色 非常的严肃认真,我在他们的权威下以保持沉默的方式来表示完全的顺从,对 他们所作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表示反抗。与我内心的恐惧完全的相反,我的阴茎 以它特有的方式声明著它的满足,龟头上渗出的前列腺液体闪闪的发亮。 接下来是让我最感到羞辱的事情,他们取出了肛门塞:就像是我的身体突然被 掏空了一个洞。仍然将我反铐著,他们不停的为我灌肠,直到流出的完全是清 水,我的身体里空空如野并且乾乾净净。灌肠完了後,博搬来了一个餐凳,让 我坐在上面。他们将我的脚和凳子紧紧的绑在一切,然後用了一条长绳子绑住 我被铐著的双手,用力向下拉紧,从凳子下面穿过,用剩余的部分绑好我的生 殖器,这样如果我的手有动作的话,将会给我的生殖器带来很大的痛苦。金拿 出一个电动剪刀对我说,由於我对博的短发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准备 将我的头发也理成那样,同时他也告诉我,博的头发就是他剪的,而现在他们 认为是一个恰当的时刻。博这时让他先等等,认真的对我说:由於我现在还没 有完全的真正的属於他们,所以他们要徵求我的意见。这可能是他们整个周末 唯一徵求过我的想法的事情,但是他们可能并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他对我笑 了。我是否需要理一个他们喜欢的发型,他们想听听我的回答。 “我愿意,主人,”我对博说,一点都没有犹豫,然後又重复了一次:“没有 任何问题,主人。” 当那把剪刀碰到我的头的时候,我的笔直的阴茎向上跳了一下,然後我安静的 看著我的头发从身旁落下,掉到地板上。 理发後,他们又给我戴上了头具和口塞,并加上了一个眼罩。他们告诉我并不 用急於看看我剪发後的模样,不过他们告诉我,现在我看上去很酷而且很可 爱。我体会著现在带著头具和先前留著长发时带著头具的不同的感觉,好象现 在头具可以把我的头部箍得更紧。我的嘴必须张得更开,那个橡皮球好像更加 深入到我得喉咙里了。他们将我从凳子上松开,打开手铐然後又把我的手铐在 前面,然後让我站在淋浴得架子下,他们将我被铐著的双手举的高高的,挂在 头顶上的一个钩子上。我的身体其实已经很光滑了?还腔故墙掖油返? 脚的体毛都用剃刀剃乾净,连腋窝都没有放过。他们然後在我的全身涂上了一 种味道怪怪的乳剂,包括我的睾丸和阴茎的根部,他们解释到这是脱毛剂,让 我等一下让它发挥作用。他们然後又想起了什么,让我转身面对墙壁,将那种 怪东西又涂在我的屁股和肛门上,有一段时间,我的睾丸,阴茎,肛门等敏感 的部位好像是著了火一样难受。因此当他们用凉水将我的全身冲洗乾净的时 候,我的阴茎完全的软了下来,缩成了一团,这可能是自从我遇到他们以来的 第一次。(未完待续)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兴奋之前,他们给我穿上了一条复杂的贞操装置,也就是前 一天晚上博没能够给我穿上的那一个。不过这一切是我後来才知道的,当时我 只知道他们在给我穿上什么东西,然後我发现我再也不能勃起了。我的生殖器 上包著一个厚厚的金属环。环上连接著活页,圆形的半球状的金属小笼子,覆 盖著我的生殖器然後用六角螺丝和金属环锁在一起。我的阴茎被折叠著和睾丸 挤在一起,然後被笼子强迫的指向下方;笼子很小,我的阴茎和睾丸被压缩到 了一块。 他们擦干我的身体让我弯下腰,再次插入肛门塞。他们带著我走出浴室,解开 眼罩,继续将贞操带完全的安装好。除了阴茎环和笼子以外,贞操带还由多条 的皮带和钢质的连接物组成,从腰部开始向下绕过我的臀部,支撑我的屁股, 然後还有一条沿著我的屁股缝压住我的肛门和肛门塞,连接到阴茎环的底部, 在前面,笼子的上部由皮带向上和腰带连在一起。他们让我作了几个动作,立 正,下蹲,向前倾斜,来测试在不同的姿势下皮带的松紧度,并把它们完全的 固定好,然後在各个地方都上了锁。这是一种永久的感觉。我的阴茎在他们重 新插入肛门塞的时候就开始膨胀,而当他们将贞操带的皮带收紧的时候更是持 续的想要勃起。金说我的阴茎有点不受控制,因此需要被调教一下,完全的勃 起只有在他们允许的时候才可以,那时他们才会打开贞操带。它显然有了反 应,它的头部用力的挤压著笼子坚硬的内壁,我认识到笼子带来了无可比拟的 受虐的感觉。不知不觉的我的双脚发软,被堵的严严实实的嘴里发出了呻吟 声。他们相视而笑,告诉我我将会适应这种感觉,并且警告说如果我再制造噪 音的话他们就会换一个更大的口塞。 现在他们将我带到了墙上的镜子前,鼓励我好好的欣赏一下我的身体:几乎是 裸体,平头,戴著手铐,堵著嘴,屁股里插著肛门塞,阴茎和睾丸被压缩在笼 子里,身体上所有的洞穴几乎都被充满,完全受到他们的控制。我尽力克制住 呻吟,从口塞的缝隙和鼻孔里喘气。他们打开了手铐,换上了两套固体的铐 子,一副在肘关节上面一点点的位置锁住我的双臂,另一副铐在我的手腕上, 这使我的双臂分离,双手相连在背後只能保持住一个姿势,几乎无法作出任何 动作。他们有用了一个类似的装置铐住我的脚踝将我拖到了墙角的一个大木箱 旁边。我早就没有了时间的概念,只能根据我的身体的判断知道现在大约是下 午的1到2点钟。我的印象中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他们下午要去处理一点事情 要到晚上才能回的来。当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保证我的安全。金打 开箱盖,然後他们帮助我坐在箱子的边缘上将双脚慢慢的移进了箱子。箱子里 装满了小块的泡沫塑料,他们帮我在这些包装物里挖掘,直到我的双脚接触到 了箱子的底部,金按住我的肩膀,帮我慢慢的坐下,而博在一边帮忙将那些塑 料泡沫挖开然後堆在我的身上,最终,我坐在了箱子里面,上半身靠著箱子的 侧板,膝盖顶著胸部,我的头部正好和箱子的顶端平齐。他们在头具和口塞的 外面又加上了一个皮面具,收紧了绑带。我可以感到他们在箱子里面加了更多 的塑胶泡沫?椋蛳卵菇袅艘恍K侨梦以谙渥永锩婊疃硖澹ㄊ率瞪希? 也只能移动上半身),将那些泡沫松动一些,然後继续地添加泡沫塑料,直到 箱子里面塞地满满的,而我也无法向任何方向移动我的身体。泡沫一直堆到了 我的下巴。 这里我必须中断一下我的故事来详细的描述一下这个箱子,那实际上是一个包 装用的板条箱,是用厚重的木板制成的,只是金和博改变了它的用途。它有两 个盖子,一个盖子上有一个缺口,直接盖在泡沫上面,刚好可以让囚犯的脖子 露在外面,另外一个则是完全的一整块的固体,将箱子密封的严严实实。两个 盖子都是和箱子完全分离的,但是当它们盖上以後,可以轻而易举的用挂锁将 它和箱子完全的扣牢。他们在箱子的侧面和顶盖上钻了不少出气孔。那天当我 被关在箱子里的时候,即使皮面具削弱了我的听力,我也清清楚楚的记得当内 盖关上时木头发出的撞击声和铁锁在木盖上刮出的声音。他们中的一个将内盖 用锁锁住,这使得那些包装物的压力更大,箱子里的空间也更小。然後是另外 的一个让人痛苦的声音,使我在这种处境下感受到一个真正的奴隶的感觉,箱 子的顶盖砰的一声关上了,突然的气流使我的头脑嗡嗡作响。